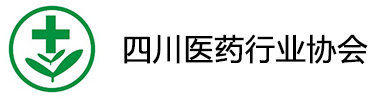青蒿素(蒿甲醚)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醫藥研究人員發明并在國際藥學界最負盛名的一只首創抗瘧新藥。它是由中國科學家自主研發并擁有知識產權的藥物之一。自從中國生產的青蒿素首次登臺亮相并獲成功后,聯合國衛生署不再采購那些無用的奎寧類抗瘧藥老產品,而是采購青蒿素將其分發給非洲瘧疾疫區病人使用。2004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剔除抗瘧藥一線用藥氯喹和伯奎兩只老產品,而將青蒿素作為一線抗瘧藥產品推薦給各國臨床醫學界。這也是中國藥物再次在國際醫藥舞臺上大放異彩。
周邊國家搶“飯碗”
由于全球瘧疾患者數量龐大,故對于青蒿素生產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塊巨大的“蛋糕”。提取青蒿素的主要藥用植物是我國特有的黃花蒿。在2004年青蒿素在國際醫藥界嶄露頭角時國內好幾個省掀起了種植黃花蒿的熱潮。因為按照常規用量計算,國際市場對青蒿素的需求量最保守估計也要250噸左右,為此我國重慶的酉陽縣政府將種植黃花蒿作為幫助當地農民脫貧致富的主要方式。至2014年,酉陽縣全縣種植了8萬畝的黃花蒿,按保守估算這些黃花蒿最少可提取出60噸的青蒿素成品。不僅酉陽,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也成為國內主要黃花蒿種植基地。因為這里出產的黃花蒿含青蒿素較高。目前,該州種植的黃花蒿最低也能提取出20~30噸的青蒿素成品。此外,湖南、廣西、福建和浙江等南方省也有一定數量黃花蒿種植面積。
有關部門估計,全國青蒿素實際產量在110噸左右。隨著全國性“青蒿素熱”的興起,十幾年前全國各地約有一百多家植物提取物加工廠從事青蒿素生產。但青蒿素熱來得快也去得快,由于當時黃花蒿供不應求,一些不法農戶將青草粉混入黃花蒿粉中提供給青蒿素生產廠造成成品雜質含量高且質量低下等惡果。加上國際市場青蒿素銷路不佳,故最終中國青蒿素原料藥在國際市場銷量直線下降,不少青蒿素提取加工廠因此倒閉。
造成國產青蒿素在國際市場銷路不暢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國周邊鄰國如印度、越南、泰國和印尼等這些國家的氣候土壤也適合種植黃花蒿,且這些國家的人力成本大大低于我國。故近年來印度、越南也在大力推廣種植黃花蒿并出口青蒿素原料藥粗品。國外廠商甚至直接在印度和越南設廠,從黃花蒿中提取粗品青蒿素再運回國家加工,從而放棄了在中國采購青蒿素粗品。
正是由于中國周邊國家搶走了中國青蒿素生產商的“飯碗”,最終導致國內很多家青蒿素提取加工廠的倒閉。據國內有關部門估計,近年來我國已有約7成左右的青蒿素提取加工廠關門。有消息說,目前我國生產的青蒿素在國際市場上僅占5%左右份額,而印度則后來居上,其青蒿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很大比重。以諾華和賽諾菲兩家為首的西方大制藥公司,則以極低價格收購印度或越南的青蒿素粗品運回歐洲進行精加工,并進而加工成青蒿素復方制劑銷往非洲瘧疾疫區。這樣一來,從黃花蒿種植戶到青蒿素提取加工廠,對中國青蒿素整個產業鏈造成毀滅性打擊。這就是為何近年來國產青蒿素原料藥在國際市場上遇冷的真正原因。
青蒿產業或陷低谷
青蒿素國際市場波動較大,目前青蒿素大用戶是聯合國衛生署,它們負責訂購青蒿素制劑并分發給非洲南部瘧疾疫區國家病人使用。但實際情況是,瘧疾發病情況也有高峰和低谷期,一旦遇到瘧疾高發年份,聯合國就會大量訂購青蒿素制劑發往非洲。而一旦非洲干旱雨水偏少且蚊蟲密度降低及由此造成的瘧疾發病率降低,則聯合國衛生署采購青蒿素數量也隨之減少,故青蒿素市場具有明顯波動性。聯合國衛生署主要訂購瑞士諾華公司和法國賽諾菲公司2家生產的青蒿素復方制劑。近年來印度仿制青蒿素復方制劑也已正式亮相國際醫藥市場并奪走了部分西方公司的青蒿素市場。這對我國青蒿素產業鏈來說更是壞消息,因為印度出口各種制劑的價格都很低。國內有消息稱,印度仿制青蒿素復方制劑已占到國際青蒿素市場的50%。
至于青蒿素市場前景,由于瘧疾有兩大高發區即非洲南部和東南亞地區,隨著青蒿素在東南亞的推廣使用,目前東南亞的瘧疾發病率已大大降低,而非洲南部國家由于戰爭和居民普遍貧窮,故瘧疾至今仍為威脅當地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而當地政府也無力改變這一現狀,只能等待聯合國的救助。事實上,聯合國衛生署購買抗瘧藥的資金大多來自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贊助,既然聯合國拿了西方國家的捐款,該組織肯定會優先訂購西方制藥廠商生產的青蒿素制劑產品來分發給非洲國家使用。這樣就能解釋,為何中國昆明制藥廠及桂林制藥廠等也能生產合格的青蒿素制劑產品且質量有保證,而聯合國衛生署卻愿意花高價訂購諾華公司和賽諾菲公司的青蒿素產品,其原因不言自明。因此在今后幾年,除非瘧疾再次大流行,我國青蒿素產業將進一步陷入低谷。(來源:醫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