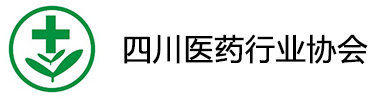▍“藥品追溯體系”重建
昨日,CFDA發布《總局關于公布國家藥品編碼本位碼數據的公告(2017年第1號)》,宣布整體公布國家已批準上市藥品的“國家藥品編碼本位碼”(以下簡稱本位碼)信息,以“方便企業推進藥品追溯體系建設”。
當日,包括163820個國產藥品和3754個進口藥品的本位碼隨即被全部公開。
按照CFDA昨日公告中的表述,2009年起,國家對批準上市的藥品編制本位碼,用于唯一標識按照藥品注冊管理辦法批準上市的與特定生產企業、藥品名稱、劑型、制劑規格等信息對應的藥品。
作為國家藥品編碼的一部分,本位碼與監管碼、分類碼共同構成國家藥品編碼體系,以數字或數字與字母組合形式表現,都具有追溯功能。
其中,此次公告中涉及的本位碼編碼由14位阿拉伯數字組成,根據應用需要,可以采用一維碼、二維碼或電子標簽等多種方式標識,可以應用于追溯碼的編制。
▍追溯碼一統天下
而追溯碼此時被重提,難免牽動市場神經。
事實上,藥品追溯和藥品監管碼曾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成為絕對的年度重要事件之一。
2016年1月25日,民營藥店湖南養天和大藥房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起訴國家食藥監總局強制推行藥品電子監管碼,不僅違反了《招標投標法》的規定,還涉嫌行政壟斷。
隨后事件迅速發酵,關于國家食藥監總局強制推行這一政策的背后深層動因,以及當時獨家運營藥品電子監管碼的阿里健康都開始受到關注與質疑。
2月20日,食藥監總局發布暫停執行《關于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全面實施藥品電子監管有關事宜的公告》;21日晚間,阿里健康發布公告稱,正在與食藥監總局進一步討論該事項,并成立一個聯合工作組以討論藥品電子監管網的移交事項。
但對監管碼曾經發揮的作用,CFDA給出了充分的肯定。
來自CFDA的信息顯示,2013年乙肝疫苗致初生兒死亡事件后,有部門通過藥品電子監管網數據排查,召回了4000萬支疫苗;2014年以來,國家食藥監總局通過對藥品電子監管數據流向分析,組織對部分藥品批發企業實施了含可待因復方口服溶液、含曲馬多復方制劑等藥品的專項飛行檢查,查實了近20家藥品批發企業違法銷售此類藥品致其流入非法渠道的行為;2016年,食藥監總局通過藥品電子監管碼發現7家企業非法回收藥品。
但這并不能改變整個事態的走向。
4個月后的2016年6月,阿里健康移交脫離全國電子監管碼,并正式上線了以藥品電子監管碼為基礎建設開放的、市場化的第三方追溯平臺——“碼上放心”,這一圍繞監管碼的全國性市場爭論才終于恢復落定。
昨日,有長期觀察這一事件的分析人士向賽柏藍表示,盡管監管碼被暫停,但CFDA對于藥品追溯的想法一直非常明確。
“追溯是必須要做的,國家藥品編碼的三種編碼都有追溯功能,現在看來,與注冊信息直接相關的本位碼可能是最符合這個功能的載體。”該分析人士表示。
實際上,早在2016年監管碼事件尚處于輿論風暴中心時,業內很多意見都已經提出了將藥品批號與追溯功能結合的想法。
“原告方”養天和大藥房董事長李能就曾公開建議,“將現有的條形碼和藥品批號合起來,在公平開放的平臺上做藥品追溯體系更科學。”
而更大的思路轉變在于政府監管與企業責任之間的切換。
2016年9月,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總局關于推動食品藥品生產經營者完善追溯體系的意見》,明確表示,“食品藥品追溯體系是食品藥品生產經營者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食品藥品生產經營者應當承擔起食品藥品追溯體系建設的主體責任,實現對其生產經營的產品來源可查、去向可追。在發生質量安全問題時,能夠及時召回相關產品、查尋原因。”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國藥品追溯的問題發生了核心變化,即從政府主導建設藥品追溯體系轉變成由企業負責。這就意味著,藥品追溯和監管變成了企業在日常經營中的責任。”阿里健康副總裁王培宇此前在中國醫藥產業高峰論壇上接受賽柏藍專訪時表示,其自建的市場化開放追溯平臺進展順利,目前已經有3000家生產企業進駐,并擴展至了非藥品的食品、保健品等行業。
他判斷,從未來判斷,追溯一定是跨平臺模式的功能,通過采集數據引發更多的增值服務,一定不是一個企業能夠做的事情,需要多方參與,將平臺運營的成本降下來,實現更高效的追溯與管理。(來源:醫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