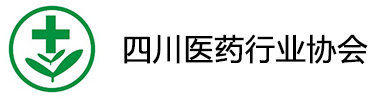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克服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的傾向,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意見》提出,力爭通過3年時間,基本完成工程、衛生、農業、會計、高校教師、科學研究等職稱系列改革任務。同時,《意見》要求,要重點考察專業技術人才的職業道德,突出對創新能力的評價,合理設置職稱評審中的論文和科研成果條件,對職稱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考試不作統一要求。
職稱制度改革終于一錘定音,衛生職稱的改革赫然在列!事實上,對于廣大基層醫生來說,職稱評定的改革早已拉開序幕。
長久以來,一心專注于臨床的醫生們發論文、考外語和計算機成為評職稱的“鐵律”,不僅使醫生疲于應對,還衍生了大量論文造假行為。而這些硬性要求也讓基層醫生的晉升之路顯得尤為艱難。
過去兩年,各地陸續有文件出臺,基層醫生職稱評定擺脫了這些硬性的束縛。評職稱更容易了,含金量降低了嗎?基層醫生在醫療體系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基層醫生職稱評定門檻降低了
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工作怎么做?遼寧省的相關文件是在2016年11月30日出臺的。明確從2017年開始,取消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外語、計算機能力要求、論文硬性要求。與此同時,也降低了正常晉升的學歷要求。
遼寧省該文件的出臺并非偶然。
“基層醫生評職稱要交論文是花架子。”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
蘇北人民醫院院長王靜成當時這樣向總理諫言:“醫生的職稱問題,對部省級以下的醫院像地市級醫院,完全應該把評職稱的自主權下放,不要統一的都要交論文、考外語。醫生的技術能力、服務水平,最重要的是讓患者滿意。讓醫生把精力主要用在寫論文、考外語上,對地市一級的醫院完全沒有必要。”
這便是基層醫生職稱評定中取消外語、計算機能力、論文硬性要求最大的意義。
事實上,此后,從國家到地方,紛紛對這一頑疾“下狠手”。2015年10月,浙江省衛計委發布了《關于深化衛生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制度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與《關于深化衛生技術職務評聘制度改革有關具體事項的通知》,提出下放審批權限,采取分類審批等舉措。
2015年11月,國家層面重磅出擊。人社部和國家衛計委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從健全評審體系、優化評審條件、完善評審標準和建立長效機制等方面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聘工作,不再將論文、職稱外語等作為申報的“硬杠杠”。
與此同時,強調評審指標要“接地氣”。對縣級醫療衛生機構和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評審標準有所區別,重點加強對常見病、多發病診療、護理和康復等任務,以及公共衛生服務等任務的考核評價,實現“干什么評什么”,避免職稱評審和實際工作出現“兩張皮”的現象。
“門檻降低了。”天津市北辰區西堤頭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趙輝介紹說,基層醫生對這一措施都比較擁護,以前很多基層醫生也想考高級職稱,但是因為要求比較高難以如愿。如今,隨著門檻的降低,好多醫生考高級職稱的欲望強烈了,無形中提高了這個隊伍的整體素質,最終提升了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
據健康界不完全統計,繼國家指導文件出臺以后,湖南、江蘇、安徽、陜西、云南等地陸續出臺類似文件,讓當地基層醫生職稱評定從英語、計算機、論文這些束縛中解脫出來。
更容易得到的職稱 含金量如何?
然而,面對更容易得到的職稱,也有人質疑會降低基層大夫們的業務水平。
有分析指出,這一舉措會使基層醫生對于醫學領域新技術、新知識的儲備越來越少,雖然有到上級醫療衛生機構進修的機會,但與大醫院醫生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針對這一問題,常年在基層工作的全科醫生李明(化名)通過健康界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他認為,首先,老百姓不關心基層醫生能不能說英語,也不在乎大夫發多少文章,他們關注的是醫生能不能解決病痛;此外,據目前而言,中國的全科醫生完全能夠通過國內專業醫生和資料來提升服務水平;而計算機和科研,對于基層醫生處理問題的能力顯然不是一票否決式的。
關于含金量,趙輝認為,以前基層醫生晉升職稱的時候,主要是為了取得職稱的稱號,真正職稱匹配什么樣的水平,并沒有特別看重。而隨著分級診療的實施,基層醫療機構不再是“大藥房”。對于基層醫生而言,能夠看到更多有質量的患者,也有了更多的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們也在逐步轉變觀念,由過去不看含金量,變成現在必須要看含金量,“如果沒有相應的技術做支撐,就算給了一個副高的職稱,也不能與崗位相匹配”。
另一個疑問是擁有高級職稱的基層醫生的流動性。目前,即使擁有職稱,基層醫生想要上調到大醫院也并不容易。國家文件在“長效機制”部分特別指出,“取得基層衛生專業高級職稱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原則上應限定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聘任,由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上級醫療衛生機構流動時,應取得全省(區、市)統一的衛生高級職稱”。
雖然天津的有關政策還沒有出臺,但據趙輝透露,在這一點上,天津將與國家文件保持一致。
這種限制并不稀奇。趙輝介紹,在天津近年來的醫改中,基層醫生注冊為全科醫生后,調入上級醫院就有一定的限制。
據健康界統計,目前在各省份的跟進文件中,關于“長效機制”的論述各不相同。
以遼寧省為例,“各地各部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基層衛生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做好崗位設置、崗位聘任、工資待遇等相關工作,建立基層衛生高級職稱改革的長效機制。”由此可見,想要從這樣的表述中看到具體操作路徑,著實很難。
更多的省份則是參照國家的指導文件,由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市州及以上醫療衛生機構流動時,應取得全省統一的衛生計生系列職稱。
基層醫生做好健康守門人還需標準細化
盡管實施起來道路崎嶇,但解除基層醫生評職稱枷鎖,仍然被認為是強化分級診療的重要一環。
“新的規則不僅讓你留在基層,大醫生還要下基層,從而削弱大醫院虹吸的力量。”趙輝認為,過去醫生們想去大醫院上班,主要是基層難以見到疑難重癥,自己的技術能力會退化,“未來隨著基層醫生待遇的提升,分級診療的實施,這一點會有很大的改變,基層醫生會對自己的崗位越來越充滿自信。”
對于基層醫生評職稱的改革,李明認為:“非常地好!”,但應該是先有新標準然后再取消原有標準。
李明表示,要想基層醫生真正做好健康守門人,新政策剛性標準亟待完善。他坦言,把實用性相對較差的原有標準撤掉以后,新的標準夠不夠高,執行標準是否夠嚴格,能否服眾,這些都至關重要。
即使現在醫生以病例來代替論文評職稱,細則的制定也并不簡單。李明以一個例子說明了事情的復雜性。
幾天以前,李明的同事接診了一位患者,這名患者曾在大醫院心內科就診,診斷有輕度心衰。但到了社區醫院后,李明的同事發現患者貧血是心衰的誘發因素之一,隨即讓患者血常規檢查,追問病史得知患者有長期消化不良,又查了消化道腫瘤標志物。雖然這名患者最終還要回到大醫院,但是這個“沒有明確診斷、沒有實質性治療”的病例是否反映了基層醫生的醫學素養和理論水平?
“職稱評定是一種能力考核,勢必要有量化標準,過去考外語和計算機是把事情簡單化了,而現如今應先有新的評價標準出臺,然后再取消原來的標準,從而實現評價標準的合理過渡。”李明坦言。(來源:醫藥網)